主角祁夜容程暖尹小说祁夜容程暖尹小说全文免费阅读(免费)+(番外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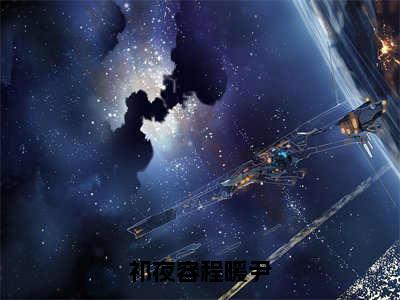 心陡然一沉,涌上无尽的慌意。 心陡然一沉,涌上无尽的慌意。
怎么会…… 纪云惜不敢置信,她怎么都想不通,自己为何要那样卑微去乞求一个自己讨厌了一辈子的男人的欢爱! 她的心口,至今回想那个片段都会传来浓切的刺痛之意。 纪云惜不解,却又无从解释自己的行为举止。 末了,她整个人颓了下来,往床上一躺。 “秋兰,你先退下吧,我想休息。” “是。” 待侍女退下,纪云惜目光沉沉落在自己手背上早已成疤的痕迹,长长叹了口气。 …… 另一边。 傅承安出门后,便直接去了侧院。 孟月莞正等在屋内,见傅承安过来,她当即上前来。 “相国,妾身已经听下人说了,听说姐姐是重伤过后,记不起很多事来了?” 傅承安神色复杂,点点头:“是,所以刚刚她对你的无礼之处,还望你能多多体谅。” “夫君这是说的什么话,妾身何时是那般小气之人?” 孟月莞娇嗔一句,便是坐入了傅承安的怀里。 傅承安身形微顿,却并未推开,“还是你体贴,这段时间亦是辛苦你了,我和云惜在宫里,这府中的一切就多亏有你。” “我嫁入相府,这都是我应做的。”孟月莞姿态柔和,尽显温婉。 傅承安的眉头舒展不少。 孟月莞当即递上一杯茶水,悄然凑近:“夫君,那今夜你可否留在我院里?” “云惜病伤未愈……”傅承安的眉头蹙起,下意识要拒绝。 可下一刻,孟月莞的手柔弱无骨攀上了他的肩膀,附耳吹了气:“夫君σσψ,你我半月未见,姐姐如今身子不能伺候你,她身旁也有侍女照顾,你不如就全了妾身的思念,可好?” 孟月莞的声音轻柔,与纪云惜全然不同。 看着孟月莞那楚楚可怜的模样,傅承安的耳根子发软,终究还是点了头。 “好。” 闻言,孟月莞神色正是一喜,却听傅承安旋即却又道:“不过,之后你就待在侧院里少出门,也少出现在云惜面前,惹她生气,这相府,说到底她才是夫人,你莫要越权。” 此话便是带着隐隐的警告之意了。 孟月莞神色一僵,垂眸点头应:“是,妾身知晓的。” 只是低头时,她的眼底闪过一丝恶意。 之后一连几日。 傅承安都去忙着处理公务,到傍晚时才归来。 一回府,他便赶来主院和纪云惜用膳,到了夜间,侧院便遣人过来,又将他喊去了侧院过夜。 纪云惜将这些尽数看在眼里,心里却并无甚情绪。 有时,她都很想问一声,傅承安不累吗? 当然这话她只在心里想想,并未当真问出口,她知道若是问了,恐怕又是惹来一阵争吵。 很奇怪。 自从这场重伤醒来后,纪云惜明显感觉自己的精气神已经疲惫许多。 她再没有从前那样的精神想去跟傅承安大吵大闹,也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找他的麻烦。 纪云惜做什么都觉得累,脑子里依旧是一团乱麻。 记忆这团乱麻未解开之前,她的心里总是堵得慌,对什么都不起劲。 偏偏,她再如何努力去想却还是想不明白。 又是一月过去。 时间已入盛夏,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。 纪云惜心口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,不再渗血,开始结痂,她亦能下床走动了。 遣退下人,她独自在庭院的阴凉处待了半晌。 天色渐晚。 纪云惜隐约闻见了从祠堂传来的香火味。 思绪微顿,她似乎许久未进去祠堂,或许抄抄佛经,倒能静心。 这般想着纪云惜便动身直接去了祠堂。 刚踏入,抬眼入目却让她神色骤然一紧。 那是——她爹爹的灵位! 有什么轰然在纪云惜的脑海里炸开! 一抹怒意直冲头顶。 纪云惜红着眼睛,转身持剑便冲去了傅承安的书房。 傅承安的笑意在注意到纪云惜手中的剑时戛然而止。 他眉头一拧,“夫人,你这是做什么?” 下一瞬。 纪云惜一把将剑对准了傅承安,冷声质问—— “我爹何时去世的?你为何要瞒着我?!”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