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不及说的爱(裴茹雪杨信生)全文小说免费阅读_(裴茹雪杨信生)来不及说的爱最新章节列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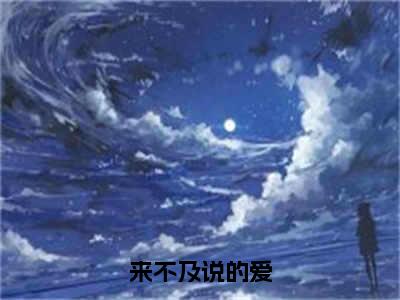 4. 4.
“走?” “你舍得?” “7年前你为了那笔钱,才住进了我的别墅。到现在你没有多拿一分钱,你舍得走么?” 裴茹雪很快从失态的情绪中走出来,她一副看破了杨信生的模样:“你在我这儿熬这么多年,不就是想熬到我心软,和我结婚分我的财产?” 一句句冷冰冰的话,似北方冬天的寒流将他席卷,让他又回到了那个窒息的冬天,几乎喘不过气。 “我不明白啊裴茹雪,你为什么总觉得我在贪图你的钱?这7年我若有半分贪图,何至于苦挨着不走,被你折磨到现在?我为何不趁着年轻去找其他有钱的女人碰碰?” 他费解地看着那张带了恨的脸,他不明白,都7年了,她还没有消气吗? 她咬牙切齿,眸间满是遮不住的恼色:“你少装了,不是钱,你还能是为了什么?你在我们最穷的时候把我甩了,又在我发家之后回来,我有多蠢才能看不明白?” “你熬了7年,发现水磨工夫对我没用,所以今天才改变策略是不是?你故意往死里喝酒让我心疼,又故意可怜兮兮地拿出那本账,我险些还真的被你给骗了!” 她冷笑起来,失控地过去揪住他的脖颈:“你消失7天,把自己弄成一副病恹恹的惨样,不就是在为这个计划铺路?” 杨信生笑了,笑得发苦,哭得说不出一句话。 他以为她根本懒得多看他一眼,没发现他的病色。 现在才知,他在她心里,已经是回天乏术了。 他就是说出真相又怎样?她脑子里有一万种思路将他诬化。 现在他已经不欠裴茹雪了,又何必在乎她怎么想呢? 他抬手想推开脖子前,裴茹雪根本没舍得用力的手。 可方才激动的情绪给他身体带来的负担,在这一刻突然发作。 他疼得跌倒在地,蜷缩着止不住地发抖。 昏黄的灯光照在他额前的细汗上,显得他苍白的脸色更加危险可怖。 “阿生,我......我也没用力啊!” 看着疼到连呻吟也喊不出声的杨信生,裴茹雪慌乱得不知所措。 她跪倒在他身前,想安抚他,却又怕加重他的痛苦。 她急得掉了泪:“阿生,你到底是怎么了?是喝多酒,伤到了胃么?” 他想说,是爱错人,伤到命了。 他不怕死,但他不想到死都在这个困了他7年,令他窒息的别墅。他艰难地挤出一丝沙哑的声音:“药........茹雪,给我止痛药。” 那年冬天他冻伤了身子,便在家里常备一盒。 他吃药的时候还被她瞧见过,她知道止痛药的位置,可却跪在地上迟迟站不起来。 “阿生,我现在让琼姨给你去买药好不好?” “或者我干脆直接送你去医院?” 她看见他疼得身上都流出了汗,棉麻睡衣被浸出显眼的黑渍,她不敢再拖下去,弯身想将他抱起,却被他狠狠推开。 杨信生记得,家里的止痛药还有大半盒,裴茹雪为什么不去拿? 他想到了方明虚弱生病的模样,大概是发烧了。 他猜到她心里有方明,便顺手把药拿给心上人了。 过去7年,无论裴茹雪往家里带多少男人,无论当着他的面做什么,他的心都没有这么痛过。 他知道裴茹雪只是逢场做戏,只是为了折磨他,他知道她从来没有对谁动过心,再完美的男人也没有一个能在她身边待过3个月。 可方明不是。 他想起她第一次带方明回家时,没有抱住对方激烈地做些什么。 她挽着方明的手,笑眼温柔地将对方带到餐桌旁,亲手给他煮了粥。 他从她看方明的眼眸中,找见了10多年前她看见自己时,那般清澈不包含任何杂质和算计的爱。 现在他疼得要死,救他的药却被她送给另一个人。 他觉得他的心像是被撕裂,身体那般生不如死的疼,也不算什么了。 “别管我,你别管我!” 他咬牙喊了出来,靠意志推开裴茹雪,趴在地上,推着行李箱一点一点往外爬。 他像一只倔强的蜗牛,缓慢又拼了命地蠕动。 他的身影让裴茹雪的眼眶越来越红,她紧紧抓着心口也无法保持冷静,她张着嘴却许久发不出一点声音。 她不明白,以前那么听话那么隐忍的杨信生,为什么突然发了疯般地要走? 他不是一直等着她回头吗?她现在怕了,她弯下身子主动去碰他,他不该欲拒还迎地哭一哭,然后感动地将她抱在怀里吗? “杨信生,你到底想要干什么?” 她颤抖着拦住他的路,死死抓住按住他的行李箱,一双发红的眼睛深深盯着他的脸:“你不就是想要我的钱吗?好,你要多少?我给你!我都给你——” 他的眼泪打断了她的话。 她没有从那双泪眼中看见半点得逞的欣喜,只有无声的哀伤,却宛若惊雷在她心中炸响。 “裴茹雪,你终于肯原谅我了吗?” “可是我要死了。” “我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了。我不要你的钱,我只想告诉你,我半点也不欠你的了。”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