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瑾年陆雪怜小说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(常瑾年陆雪怜完结)常瑾年陆雪怜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
|
当即红了眼圈,她看看陆雪怜,摇摇头:“我不想让嫂子误会,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” 听她这意思,仿若是常瑾年不在家的这段时间,陆雪怜欺负了她似的。 陆雪怜的脸色微沉:“徐医生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 可徐诗雅却只是咬着下唇,不多说了。 见状,常瑾年看了一眼陆雪怜,旋即接下徐诗雅的行李,向她保证:“诗雅,你放心,这个家里还轮不着别人做主!我让你住下你就安心住下!” 说着,他拉着徐诗雅回了屋里。 独留陆雪怜怔在原地,她紧紧抿唇,许久才迈步回屋。 直到晚上。 吱呀一声,常瑾年推门而进。 两人同躺在一张床上,可谁都没有说话。 最终,陆雪怜忍不住问他:“常瑾年,这六年,你真的有把我当妻子看吗?” 身后的呼吸声重重一沉。 旋即,她却听见常瑾年讽笑问她—— “那你呢?你又有把我当丈夫看吗?” “你要去西部这件事为什么不跟我商量?” 第7章 这话一出。 陆雪怜身形僵住,坐起身来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 月光从窗户打下来,照在常瑾年冷沉的脸色上。 “诗雅在医院里听说的,如果不是她告诉我,你是不是就不打算跟我说这件事了?”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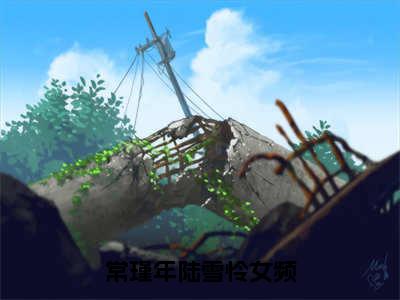 四周安静得过分。 陆雪怜望着他,许久才轻扯了下唇角:“我的事情,为什么要跟你商量?” 闻言,常瑾年眼眸一瞬冷冽,磁性的嗓音中压抑着怒气:“我们是夫妻!我们是一家人,这怎么能是你一个人的事?” 这话听在陆雪怜耳里却只觉得可笑。 她红了眼圈,定定望进他眼底:“常瑾年,那你每回有事,跟我商量过吗?” 他甚至今天才当着徐诗雅的面,说她陆雪怜在这个家做不得主,是‘别人’。 此刻却要来追究她去西部的事…… 两人的视线在皎洁的月光中对视。 许久过后,常瑾年阴沉着脸色翻身下床。 “今晚我去部队睡,我们都互相冷静一下吧。” 说完,他开门离开。 房间里恢复宁静。 陆雪怜盯着紧闭的房门许久,才重新躺下闭上了眼睛。 一夜无眠。 次日清晨。 陆雪怜照常洗漱,准备去上班。 只是在出门时,迎面却撞上刚值夜班回来的徐诗雅。 陆雪怜本想掠过她离开,徐诗雅却开口:“嫂子,你和瑾年昨晚是不是吵架了,昨晚他来医院找我诉苦时那个样子,我看着都心疼。” 原来昨晚常瑾年离开家后,根本就不是回部队,而是去找了徐诗雅。 或许是心早已被伤到麻木。 此刻,陆雪怜听见这话,竟不觉得意外,仿若本该如此。 她注视面前的徐诗雅,缓缓一笑:“那就麻烦徐医生,以后多照顾一下他了。” 说完,她不顾徐诗雅的诧异,绕开往外走。 “我快迟到了,先走了。” 一路到了科学院。 谁料,陆雪怜才刚走进院,同事王姐便凑了上来,好奇的问她。 “雪怜,我刚刚看见你爱人去找院士了,这是有什么事啊?” 陆雪怜身形当即僵住:“什么?常瑾年来找院士了?” 她猛地意识到什么,慌忙转身就朝院士的办公室跑去。 刚到门口,陆雪怜便听见常瑾年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。 “……所以我希望取消陆雪怜同志的派遣名额。” 轰然一下。 这话犹如惊雷迎头劈下。 陆雪怜心猛地提起,她顾不上敲门,直接冲了进去—— “院士,我没有要退出的意思!这事我会跟我爱人好好谈的。” 说着,陆雪怜沉着脸把常瑾年拉出了院士的办公室。 一直来到科学院内的一片空地,陆雪怜才撒了手。 她脸色难看至极,眼底满是怒意:“常瑾年,你无权干涉我的工作!” 这还是陆雪怜在他面前第一次这样严肃。 常瑾年漆黑的眼眸沉沉望着她:“所以你是非去不可了,是吗?” “是。” 陆雪怜不做犹豫,态度坚决。 两人对视着,耳边只剩风声刮过。 良久,常瑾年声音冷了下来,带着警告之意。 “陆雪怜,如果你执意要去,那我们这段婚姻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!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!” 说完,他转身大步离开。 陆雪怜站在原地,目光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。 如果是以前的陆雪怜,当他用婚姻做警告时,她早已慌乱起来。 可现在她却松了口气。 离婚…… 也好,等她去了西部,他们的强制离婚书也就下来了。 这样刚好,如了他的意。 回到院士办公室。 陆雪怜深深鞠躬表达了歉意,再度表明了自己前往西部的决心。 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派遣名额。 一连几天。 常瑾年都在部队,没回家。 陆雪怜则在家开始收拾行李。 七天后,科学院里一大早便举行了动员大会。 陆雪怜站在队伍里,听见前方院士掷地有声—— “同志们!明天就是我们出发的日子了,切记明早8点在院里集合。” 第8章 直到听到这个时间,陆雪怜这才意识到日子过得有多快。 终于快要离开了。 由于今天是在昌北的最后一天,动员会结束后,院士给所有人放了假,让他们好好回家跟家里人道别。 陆雪怜去了趟通讯室,给陆母打了通电话。 跟母亲道别后,陆雪怜又给在部队的常瑾年拨去电话。 接通后,电话那头的常瑾年张口便是问她:“你决定好放弃去西部了吗?” 他语气一如既往笃定。 他似乎,认定了她会为了他们的婚姻,放弃事业留在昌北。 可他这次要失策了。 陆雪怜捏着话筒,只是开口问他:“你今晚能回家吗?” 毕竟明天就要走了,她有些事还需要当面跟他说清楚。 也算是给她自己这六年的婚姻,做个了断。 常瑾年沉默过后:“好。” 挂断电话,陆雪怜怔怔失神。 或许是他失约太多次的缘故,让她此刻对他这声‘好’竟不敢再抱希望。 许久过后,她沉沉叹了口气。 常瑾年,最后一次了。 从通讯室回到家,陆雪怜打开房间带锁的抽屉。 最深处的布袋里,是被红布包裹的翡翠玉镯。 这是结婚时,常瑾年家里送她的。 她还记得当时常母拉着她的手殷切的模样。 “收了这个手镯,你就是我们常家的人了,以后你和瑾年要好好过日子。” 这些年,她也一直珍藏着镯子,还想着传给女儿、媳妇。1 现在也该还给常瑾年了。 可陆雪怜就这么在家等着,从黄昏,等到夜深。 门口安安静静,没有任何常瑾年回家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