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此我们姻缘线断,各不相欠(许南烟谢珣礼)全文免费阅读_从此我们姻缘线断,各不相欠最新章节列表言情小说在线阅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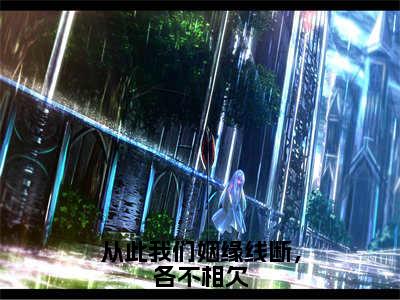 案上香云缭绕,祖师像庄严肃穆。 案上香云缭绕,祖师像庄严肃穆。
谢珣礼看见许南烟煞白脸色,心中不安浮现:“南烟,这卦怎么了?” 许南烟知道谢珣礼和谢夫人的执念,也知道整个国公府对这孩子的期盼。 她看着地上的签卦。 ‘注定夭折’这四字如重石压在心上,让她几乎喘不上气。 谢珣礼却不依不饶,沉声催促:“说。” 许南烟眼眸变换片刻,还是说出实情:“卦象显示,这孩子将胎死腹中。” 谢珣礼一愣,旋即变了脸:“你胡说什么!” “他只是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,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地位,你怎能这么咒他?” 他的诘问如利刃,直直插进许南烟心口。 相识至今,谢珣礼对她从来温声细语。 这是她第一次听见谢珣礼对她如此疾言厉色。 许南烟身子一晃,自虐一般又想起从前。 与谢珣礼成亲后,京城有许多人背后嚼她的舌根:“道士也能下山结婚?太清宫的人向来清心寡欲,怎么出了这么一个贪恋红尘富贵的……” 传到谢珣礼耳中那刻,他一家家上门找麻烦。 更放出话来:“我夫人是这天底下最好的人,再让我听到她一句不是,定不会轻易善了!” 他们之前从未有过争执。 偶尔有,张扬肆意的谢珣礼也会为了她,先低头。 回忆刮骨,许南烟捂住抽痛的心脏:“在你心里,我就是这样的人?” 谢珣礼也终于意识到这话太过伤人,讷讷解释:“南烟,我不是那个意思……” 偏话未说完,门外有人来报:“将军,柳姑娘突然腹痛如绞。” 突如其来,像是应了这卦象一般。 谢珣礼当即起身出去,走到门口却脚步一顿。 语气的情意凉下去:“无事的话,你便不要再出这院子了,好好为孩子祈福吧。” 许南烟浑身血液都冷凝,冻在原地。 好半晌,她才攒出几分力气,看向祖师爷,渐渐红了眼眶。 她不知道自己跪了多久,天色亮了又暗。 外面有丫鬟婆子低语传来:“夫人还要跪多久啊?” “不知道呢,将军只吩咐我们看着不准夫人出去。” “唉,听说了吗?新进来的夫人胎像不稳,将军放心不下,宫里的御医都请来了,咱们夫人是不是要失宠了?” “噤声,你不怕被下咒……” 言语如刃,划过许南烟心脏,疼得她几乎窒息…… 又煎熬了五日后。 谢珣礼终于出现,一来便上前紧紧抱住许南烟。 来力道大得许南烟几乎喘不过气,热度透过薄薄的衣料传来。 她知道不该,可心却不受控制,近乎贪恋地汲取着这久违的温度。 可下一秒,谢珣礼却贴在她耳边轻声问:“南烟,你一定有办法让那孩子平安降生的对吗?” 许南烟血液直冲天灵穴,瞬间遍体生寒。 逆天改命,为天道不容! 就算是她,也要付出等同的代价。 她颤着声拒绝:“我不能……” 谢珣礼漆黑瞳孔深不见底:“不能,还是不想?” 许南烟一张脸惨白毫无血色。 谢珣礼抬手,温柔地覆上她的脸。 “南烟,我幼时救过你,现在想来,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” “你们修道之人不是最讲因果,你就当了结因果,救这孩子一命!” 谢珣礼语气平淡,像是随口一说。 实际上却是字字句句都在提醒许南烟。 她欠了他一条命。 现在,到她还债的时候了。 许南烟的心脏像是被捅了个对穿,鲜血淋漓的疼。 幼时她贪玩跟随师兄弟下山,于灯会上走散,就在她被人贩子抓住即将卖入妓院时,是谢珣礼救了她。 她以为自己与谢珣礼天定良缘。 现在想来,不过是一段孽。 对峙良久,谢珣礼叹道:“南烟,我爱的只有你,可人活于世,不能如此由心,我还有该担的责任。” “何况战场上刀剑无眼,我若出了事,孩子也能给你和母亲一个慰藉。” 他言之凿凿,句句占理。 俊美的摸样与以往无异,眼里的情意也好像从没变过。 可许南烟看向他,却只觉得陌生。 以前的谢珣礼不舍得她受一点伤。 现在的谢珣礼却能冷着脸提醒她,恩情是要还的……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