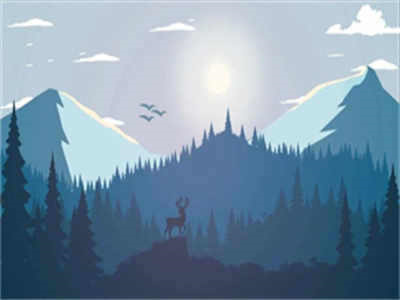姜云岁裴闻小说全文完整版免费阅读-惩娇小说最新章节
|
深,等母亲回来,她和裴闻的婚事就要被抬到明面上来,不过在此之前,侯夫人会先过问她的意思。 上辈子,姜云岁是红着脸说愿意的。 她至今也不懂那时候对裴闻是不是喜欢,只是觉得他长得最好看,虽然摸不透他的性子,但他好看就够了。 如今想想,她那时候也不太懂什么是男女之情,还没开窍呢。 八成是将裴闻当成了个好看的哥哥。 所以后来她和宋砚璟出了那样的事情,她叫父亲去退了婚,心里头却没什么难过的情绪。 — 从听澜院送出去的信,先是到了裴闻的手里,过目了一遍才又送出去。 皇后又召见了她两回,都被她称病躲了过去。 姜云岁心里清楚皇后请她过去,无非就是想逼她快些同裴闻成婚,最好是能先将生米做成熟饭,这件事板上钉钉再无转圜的余地,她才能放心。 她迫切的想巩固朝臣的势力。 皇帝的昏聩,她自是放在眼里。 若是那群文臣联合起来要逼皇帝退位,那她儿子将来可就坐不上这个皇位了。 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却也不少,个个都虎视眈眈,她怎么能不心急。 姜云岁不肯上钩,简直气狠了皇后。 既然是迟早的事情,为何不先尘埃落定?万一日后节外生枝,届时可就不好收场了。 宫里面,岑澜小心翼翼伺候着她的姑姑,不经意间提起:“姑母,澜儿也是愿为您分忧的。” 皇后扫了她一眼:“你以为我不知你心里在想什么?” 岑澜喜欢裴闻,她虽然比同龄人成熟稳重,可少女的心意藏也藏不住,她每次望着裴闻的眼神都与旁人不同。 皇后轻轻握着她的手,望着侄女这张清丽的脸,微不可闻叹了叹气:“澜儿,不是姑母不疼你,嫁给裴闻的只能是姜云岁。” 她是皇家女,是郡主。 最重要的是裴闻喜欢她。 如此,姜云岁能做的事情就有许多。 她不可能不顾她的父亲母亲,不顾其他的皇家人。 走到了绝路,她一定会被哄着杀了裴闻。 岑澜垂下眼睫,继续给姑母捏肩,分毫不满的情绪都看不出:“澜儿知道了。” 这边姜云岁打发完宫里来的人,就出门去透风了。 她今天出门穿着女装,轻纱遮脸,心血来潮买了几只风筝回府。 自打病好,姜云岁就又恢复了少女的活泼,满院子里放风筝,跑得气喘吁吁,额头冒着薄汗,一张脸自内而外透着好气色,唇红齿白特别诱人。 忽的惊起一阵疾风。 放得高高的风筝线骤然断裂,风筝在空中胡乱转了几圈,最后挂在院墙里的高树枝头上。 她望着树枝上挂着的风筝,犯起了愁。 过了会儿,姜云岁命人拿来竹竿,便是如此,依然够不着高枝。 她狠了狠心,提着裙摆竟沈要去爬树。 这可把宜春吓坏了,“郡主,奴婢去叫人来,您快下来。” 若她不小心从树上掉下来,那可怎么办? 金枝玉叶,伤着碰着,底下人也不好交代。 姜云岁上辈子被囚在一方天地太久太久,难得自由,便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 她紧紧抱着树干,不往下看倒也没那么畏惧。 风筝被吹得簌簌响,她努力伸手去够挂在树枝上的风筝,却总是差之毫厘。 姜云岁咬了咬唇,心里又有犹豫,怕才往前越过一些,脚底这根纤细的枝干就要断了。 她把心一横,小心翼翼往前走了两步,这次伸手总算是够到了被缠在枝头上的风筝。 她才舒了口气,忽的听见宜春颤抖的声音:“世子。” 姜云岁循声望去,他站在院子里,阳光轻轻扫过他的侧脸,男人肤色白皙,眉眼清俊,像一幅出尘清泠的画,更像三月枝头上欲放的玉兰花。 姜云岁的脑子里忽然跳出四个字——芝兰玉树。 说的大抵是他这样的人。 她怔怔望了他一会儿,脚下的枝干忽然断裂。 一声急促短暂的惊叫被吞没在嗓子里,她紧紧闭上双眼,已经做好了摔痛的准备,却稳稳当当落进了一个稳重的怀抱。 裴闻接住了她,双手横在她的腰间,攥得有些紧。 他又闻到了她身上熟悉的软香,怀中纤柔的身躯叫他有些不自在,他绷着冷淡的脸色,如此也看不出什么不对。 他哑着声说:“小心些。” 姜云岁方才落下,无意间抓住了他的衣襟,此刻还牢牢攥在掌心,他身上的松木冷香叫她忘记了这个人的压迫感有多强烈。 她垂着眼睫,“表哥,你先放我下来吧。” 裴闻能感觉到怀中的少女在轻轻的发颤,他以为她是被方才的事情吓坏了,从那么高的树上落下,惊魂未定,害怕也是正常的。 他不擅安慰人,半晌过后也只是说:“已经没事了,你不用怕。” 姜云岁这会儿不是怕,是觉得待在他怀中实在煎熬,压在她腰上的这双手叫她心惊胆战。 如今他已有后来位极人臣时不容忤逆的威压。 沉沉落在她心头。 她摇摇头:“我不怕了。” 裴闻垂眸扫过她的侧脸,她靠着他的胸膛,被迫待在他怀中,好似已经被他牢牢圈住。 裴闻心底竟生出一种过分的满足感。 他想将她圈在怀中,这份独占欲,好似只在她身上出现过。 裴闻嗯了嗯,过了许久才慢慢将她放了下来。 少女衣裙凌乱,发丝有些散乱,发间的朱钗轻轻打晃,她的耳垂软软的,红红的。 裴闻瞥了眼地上的风筝,“下次叫旁人来帮你拿。” 姜云岁在他面前很老实,她只想快些相安无事的度过这段时日,“嗯,知道了。” 她已经尽可能不去他面前晃,可裴闻还总是出现在她面前。 姜云岁有些烦恼。 她在心里无声叹气,这样下去,再多纠缠可就不好办了。 姜云岁又不敢太冒进,她如今每次都乖乖叫他表哥,时时刻刻提醒他,两人还有表 |